

今日精选
Apr. 2025
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中常见的商业行为,但若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滥用,极易沦为利益输送的工具,严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2023年新《公司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关联交易的规制,明确控股股东、董监高的信义义务,并增设关联交易审查程序。
然而,司法实践显示,中小股东因信息不对称、举证困难等问题,维权成功率并不高。又或者是,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关联交易不够重视,从而忽视了其合理性,被主张损害公司或股东权益。
如何识别违规关联交易?本期法讯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与相关法律法规,解析涉嫌侵犯公司或股东权益的关联交易行为。

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理想状态下,股东与董监高应当齐心协力推动公司发展,实现多方共赢。但现实中,股东之间的矛盾频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各自为政,甚至通过关联交易谋取私利,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实务中,关联交易与股东权益纠纷类型非常多,相关法律问题也较为复杂,应对的策略和法律依据也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此类纠纷类型主要包括:
该类纠纷典型的情形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向公司披露其与交易对方的亲属、持股或其他利益关联,导致交易背景不透明。例如:董事长私下以其配偶名义设立公司,并与本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但未在股东会上说明关联性。而关联股东在审议交易时未主动退出表决,利用持股优势强行通过决议。例如控股股东在股东会上对关联交易提案投赞成票,其他小股东因持股分散无法制衡。 又或者伪造决策程序,包括公司虚构股东会或董事会召开记录,伪造签字文件,掩盖未实际履行表决程序的事实。高管擅自签署合同后,补发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文件,声称已获批准。 该类纠纷典型的情形是,以远高于市场价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或以明显低价向关联方转让公司核心资产。并常常同时设置苛刻的预付款比例、延长账期或要求高额保证金,变相为关联方输送利益。 例如在合同中约定,公司需预付90%货款给关联方,但对方长期拖延交货且无违约责任。在交易中附加排他性条款、强制服务协议等,规定公司未来五年只能从关联方采购某类原材料,否则需支付天价违约金,限制公司与其他方合作。 典型案例中主要体现包括,将公司专利、商标、客户资源等无形资产以低价或无偿方式转移至关联方。如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独家专利授权给关联企业免费使用。或者虚构交易转移资金,通过虚假合同、虚开发票等手段,将公司资金以“货款”“投资款”名义转至关联方。 此外也包括,债务转嫁与担保陷阱,例如让公司为经营不善欠下巨债的关联方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或承接关联方的债务,增加公司财务风险。 此类案例主要体现为信息不透明与知情权受阻。企业通过隐匿交易关键信息,在财务报告中模糊处理关联交易细节,或将其混入“其他应付款”“常规采购”科目。例如年报中仅披露“向某供应商采购1亿元”,但未说明该供应商实为控股股东亲属控制。 同时也可能拒绝股东查账请求,以“涉及商业秘密”“资料不全”为由,拒绝股东查阅合同、会计账簿等关键文件。在股东要求查看关联交易合同时,公司拖延数月后仅提供部分删减版文件。或者直接采取财务数据造假与篡改的手段,篡改交易金额、日期或交易对象,财务部门按指示将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款项拆分至多个无关供应商名下入账,以掩盖关联交易的真实情况。 利益捆绑型关联交易是指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关联交易关系,逐步将公司核心业务或资源与关联方深度绑定,形成难以剥离的利益输送渠道。这类交易不同于单次性的资产转移或价格操控,而是通过持续性的业务安排实现对公司利益的慢性侵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持续性。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情形包括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独家代理协议等方式,使公司在关键业务环节上对关联方形成深度依赖,逐步丧失自主选择权。例如,要求公司所有产品销售必须通过关联方渠道完成,并收取高额佣金;或者通过资源深度绑定:将公司核心资源(如技术、客户、供应链)与关联方共享或交叉授权,模糊权属边界。 例如,强制要求公司使用关联方提供的IT系统,并将所有客户数据同步至关联方服务器。此种情形下将使公司退出成本高昂,往往在协议中设置苛刻的终止条件或天价违约金,使公司难以摆脱关联方控制。需特别警惕的是此类交易往往以"战略协同""生态共建"为名,初期危害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公司的议价能力和独立性会逐渐被削弱,最终沦为关联方的利润工具。 当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不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时,可以尝试向该侵权股东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需围绕“证明控股股东存在滥用权利的具体行为、实际损害后果、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来举证。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2019)民申4691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原告需充分举证被告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具体侵权行为。若证据不足(如仅泛泛指控而缺乏具体侵权事实),则可能因“举证不能”导致败诉。 若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导致公司长期未分配盈余,其他股东可以尝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4条,提起“强制盈余分配之诉”。此类诉讼需突破“公司自治原则”,核心在于证明控股股东存在恶意隐瞒或转移利润等滥权行为。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528号公报案例:法院认为,当部分股东通过隐蔽手段侵吞利润时,司法干预具有必要性。最终通过司法审计确定可分配利润金额,支持了中小股东的诉求。需注意,强制分配的前提是公司存在法定可分配利润(即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剩余利润),否则诉请难以成立。 针对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司决议,股东可以尝试依据《公司法》和《民法典》主张无效,但需要聚焦“控股股东滥用权利且实际损害公司利益”或者“关联交易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实质要件,而非单纯以“关联交易”为由。 例如,在(2017)民终416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非上市公司关联股东未回避表决,并不必然导致决议无效。需结合《公司法》第20条(禁止权利滥用)综合判定。因此,中小股东需提供具体证据(如交易价格显著不公、程序违规等),方能推翻争议决议。 股东需警惕交易中是否暗藏上述情形,并通过查账、比价、留存沟通记录等方式提前固证,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关联交易如同一把双刃剑,合规则助力资源整合,违规则引发连环风险。建议股东提前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关联交易防火墙”,定期审查公司重大合同,并保留关键证据。遇争议时,尽早启动法律程序,避免时效利益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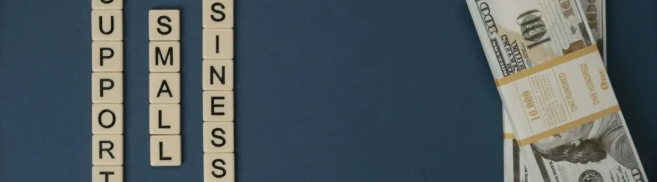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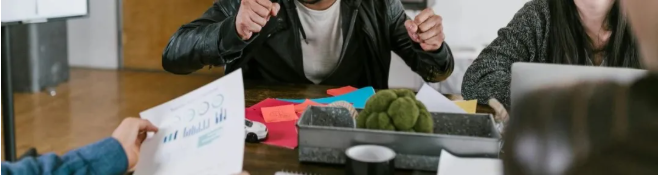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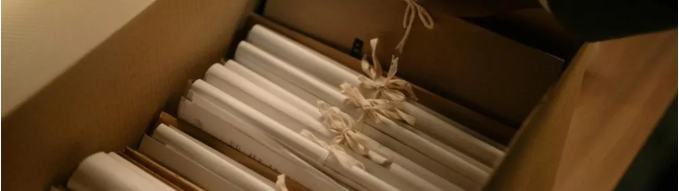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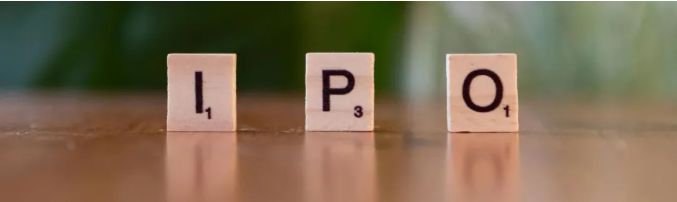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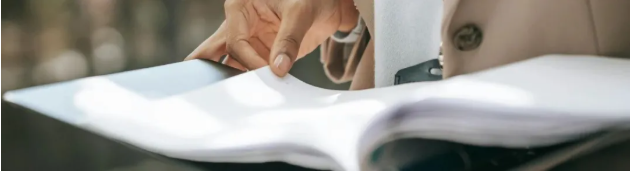




关注“海涵律师事务所”公众号
及时获取实时专业的法律资讯信息
以及对外公开培训课程

课程报名以及业务咨询